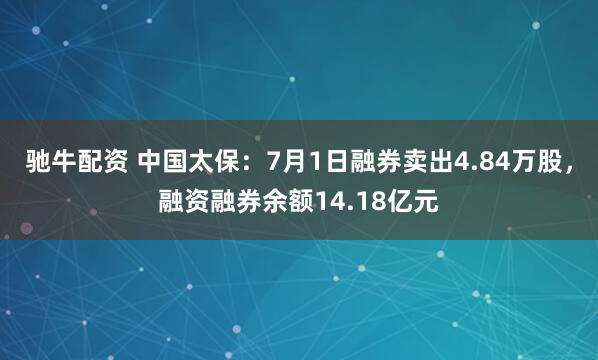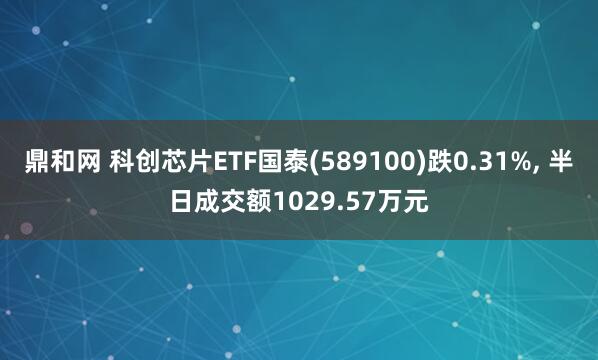日升策略
日升策略


港岛的尽头是什么?从坚尼地城的地铁站出来,乘坐小巴沿山脉盘旋而上,逐渐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,就像戴上了降噪耳机,进入一片阴凉地带,世界只剩下风吹树叶的沙响。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,也是生命意义上的。
下车地点在大口环道,对面是一所现代化的国际中学,主干道上看不见其他入口——要在转角处找到那块不起眼的横幅,往里复行数十步,才会看到目的地:香港现存过百年历史的东华义庄。
义庄,听上去是一个距离人们很遥远的词汇。你对它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林正英的港产僵尸片:主角一行人住在昏暗破败的义庄,看守无人认领的棺木,夜半无人时,自有僵尸从中跳出。直到2025年《破·地狱》加长版热映,作为取景地的东华义庄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。

东华义庄
建筑、历史、悬疑、想象…...香港是一个由神秘空间交错形成的复杂地区,这里从来不乏都市传说与类型命案,人们在具体的空间中构筑起自己对于香港的认知,而那些未曾涉足的空间,则给予了足够的想象留白。
在NOWNESS Paper夏季刊“香港折叠”专题中,我们试图走近这些空间、破除迷雾。这个过程就像拿起一把解剖刀,在切开香港不同时期的历史和社会面后,悬疑的终点指向人们内心深层的共情和恐惧——殖民的统治,逼仄的生活,无根的飘零者。
在生与死、规训与越轨、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间,香港浮现出另一面。这是第三篇,东华义庄。

Sunny 在东华义庄
5月末,NOWNESS前往东华义庄拜访。上午11点,管理员Sunny打开旧大堂厚重的木门,仍有十几副无人认领的棺木陈列其中,木板已经褪色、有些漆面斑驳,空气中只有刚点燃的线香味,这里不喧哗、不悲痛,只是沉默。
Sunny在这里工作和居住了近30年,很多人问他,不害怕和这些棺木共处一室吗?他总是笑笑说,百无禁忌。这些棺木是义庄最初成立的契机——作为停放海外华工遗体的中转站和“先人客栈”,它见证过无数海外华人的离去与归来,也因此成为都市传说和探险的源头。
进入义庄,仿佛是闯入了某个领地,但谁才是这里的主人?无人认领的华工、北大校长蔡元培、“赌王”何鸿燊、东华三院的创始人,他们都曾停留在这块陌生的空间——抹去阶层和身份的差异后,或许谁也不真正属于这里,陈列的棺木像琥珀一样,把所有人暂时冻结在离家乡最近的地方。

东华义庄见证了香港开埠至今的历史——18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后,在港岛的中上环一带兴建土木,一条太平山街,将“洋人”与沿海地区前来谋生的华人划分开来。
英治时期,华人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恶劣,鼠疫爆发后,流离失所和垂危的病人往往会选择前往百姓庙等死,同胞再将其草草葬在转角的“坟墓街”,每当暴雨冲刷山坡时,埋藏不深的棺木会被冲到路边。
1848年,美国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中国内地。在天灾和动乱持续的晚清时期,不少人选择出海谋生——太平洋连接起北美洲和亚洲,而香港作为邻近内地、可容远洋轮船停泊的港口,也成为内地人背井离乡的中转枢纽。


晚清时期,不少人选择出海谋生
赴美淘金是一场依赖时机和运气的冒险日升策略,只是好运并不经常站在他们这一边,当适龄中国男性提着藤制的手提行李箱前往加州,迎接自己的不是金山,而是漫长的铁轨。多数人因为高危工作和疾病而客死异乡,不久后,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又让剩余华人被迫迁居至唐人街度过余生。
生前无法衣锦还乡的华工,死后只有落叶归根的愿望。香港同样是他们返程必经的中转地——1875年,慈善机构东华三院在坚尼地城附近设立了牛房义庄,专为客死香港或需转运遗骸的华工提供暂时的停柩服务,这便是东华义庄的前身。
Sunny向我们展示了东华义庄至今保存的档案名册:在那个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,由同乡组成的海外华人会馆,会为离世华工提供定期捡运骨殖回乡原籍安葬的服务——会馆提前致信给义庄协调转运,东华义庄接收到海外棺骨后,在报纸刊登招领广告,同时联络各地分会馆,最终安排虾苟艇将其运回内地。

东华义庄的档案名册
顺利的话,整个过程会历时6-8个月。在上世纪末,东华义庄还需要在船上设置标旗示意,防止不明就里的海盗在途中劫船,横生枝节。
更多时候,漂洋过海回来的也并非完整棺木和遗体,而是部分骨殖,这源于旧金山华工的二次葬习俗与考量:送一个完整的人返乡至少要50美元,而如果等去世7年后再由会馆“起骨、运送与重葬”,仅需10美元,这是一道足够简单且现实的计算题。
Sunny指给我们看东华义庄外墙上的壁画,如今上面写有“落叶归根”几个字。但最后除了棺木和骨殖,有时能够归来的,只是一个空荡的藤制篮子而已。

一个人从香港乘船出发前往加州需要45天,但回家可能需要经历上百年——经过了太平天国运动、鸦片战争、淘金热、排华法案到二战硝烟散去,人与家之间的联系早已中断。直至20世纪60年代,东华义庄最多寄存了670具棺木、8060副骨殖、116具骨灰,至今仍有不少无人认领。
于是,作为中转地和“先人客栈”的义庄,开始延伸出所谓的香港都市传说——由于长期停放棺木,港产僵尸片常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义庄,而僵尸跳跃前行的动作设计,也呼应了湘西让死者归乡的“赶尸”习俗。
这种独有的中式恐怖故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流行顶峰,由林正英主演的系列港产僵尸片成为一代人的童年阴影。电影中对于“入土为安”的执念与想象,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了当时的人对客死异乡、成为无主孤魂的深层恐惧。


《僵尸先生》,1985
Sunny亦有同感,小时候社媒并不发达,自己对义庄最初的印象就来自林正英的港产僵尸片。2001年,他来到义庄正式工作,当时的环境仍相对简陋,灰色的破旧高墙和陌生的空间,“的确有让人产生联想的可能”。
十几年来,始终有胆大的年轻人试图闯入东华义庄探险,一些YouTube博主站在大门口直播、绘声绘色地讲述义庄传说。但大多数时候都没人真正进去,Sunny只记得有一次,两个年轻人在半夜想要翻墙进来,但是不小心摔伤,最后被村民抬走了。
真实的东华义庄是什么样的?他的日常工作很简单,每天除了基本的打扫巡视、花一小时为先人上香,最多就是接待拜祭先人的访客,以及“留意闲杂人等”、规劝四处张望的探险者。
唯一的例外是,Sunny有一次见两个从广州来的年轻学生四处张望,询问之下才发现原来是受母亲所托,来到义庄寻亲——他很快从整理过的档案中回忆起那个名字,已经停放了几十年的棺木,终于被后人找到。

东华义庄
不过类似的情况已经不多了。20世纪60年代,由于容纳空间有限,东华义庄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迁葬,将无主认领的骨殖迁到粉岭和合石坟场;而70年代起,港英政府大力推行火葬,普及率至今达97%,需要寄厝的灵柩及骨殖也相继减少。
如今在香港,东华义庄成为殡仪馆外唯一可以合法保存棺木的地方。Sunny补充道,目前只在三种情况下会接到少量新棺木:
“第一种是有华人相信风水、需要择吉日下葬,就会在义庄等待合适的安葬日子;第二种是香港还有3%选择土葬的人,由于墓地空间有限,在排队等待时要暂存;第三种是运往海外或内地安葬的棺木,申请批文下来之前,也会停放在义庄。”

或许是从2013年开始,香港导演麦浚龙的《僵尸》就让观众意识到,某种流传已久的传统正在走向没落——僵尸片的巅峰早已过去,华工历史不再被续写和重演。
如今,东华义庄也从最初暂存遗体的慈善机构,进一步成为陈列历史和生死教育的场所。我们跟随Sunny一路前行,义庄现在有两个停放棺木的大堂、七十二间庄房、一间骨殖仓、牌房、凉亭及花园。
2003年,东华义庄在政府拨款下进行了重新翻修,获得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文物保存及修复奖。“从老旧照片上可以看到,之前的建筑外观其实是偏灰色的,容易给人暗沉的感觉;现在调整为暖黄色调,让人觉得和谐一些,但大体是修旧如旧的原则。”

Sunny在东华义庄
东华义庄如今的运营靠上级支持,它隶属于全港最大规模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——旗下还有万国殡仪馆,当两个地方同时收到《破·地狱》的拍摄申请时,看到黄子华和许冠文的名字,“还以为要来拍喜剧”。
直至看完剧本,他们才发现《破·地狱》是试图呈现华人殡葬文化和生死观的变迁——殡仪馆的诞生,正是基于二战后人口急剧增加、空间受限,不容许人们在街道上进行各种繁复的传统仪式。
而疫情后,年轻一辈更减少对传统仪式的执着,选择简化流程,形成“院出制度”:在医院的小房间为逝者进行告别仪式后,直接运往火化场,不再需要去殡仪馆。
电影中关于东华义庄的场景,是一位母亲希望将孩子的遗体防腐封存后暂放义庄,等待日后科技“复活”孩子。而主人公文哥与道生的争执,带出人们对于死亡和背后仪式的认知变化:殡葬行业的本质是送别死者,还是告慰生者?


《破·地狱》,2024
2024年12月7日,《破·地狱》在香港上映后不久,成为华语电影票房冠军。东华义庄也再次受到关注,面向公众开放生死教育和导赏活动。
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始终秉持着客观的态度——对于殡葬,人们可以坚持传统的仪式,也有选择简化和宗教化的自由,义庄只是呈现和铭记历史的一个切面。
在东华义庄,旧大堂的左侧仍然停放着最后一副金山棺模型。Sunny指着右侧告诉我们,未来一年,这里可能会改建成一个教育展览厅——义庄每年都会与政府机构或高校文史专业团队合作,以前报名者多是对历史、建筑有兴趣的人,现在开始出现更年轻的面孔,总而言之,“这间大堂不会再存放新的棺木了。”





NOWNESS Paper 2025夏季刊邀你一起揭秘悬疑档案:为什么要伪造一个已经消失的国度?如何跟油麻地的鬼魂一起散步?如果和AI动了真情,要怎么离开这场戏?明知魔术是一种欺骗,观众为什么还要沉溺其中?听,你会如何形容一声枪响?是什么让章子怡嚎啕大哭、浑身颤抖?创造死亡搁浅的小岛秀夫,也会害怕死亡吗?




天盛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